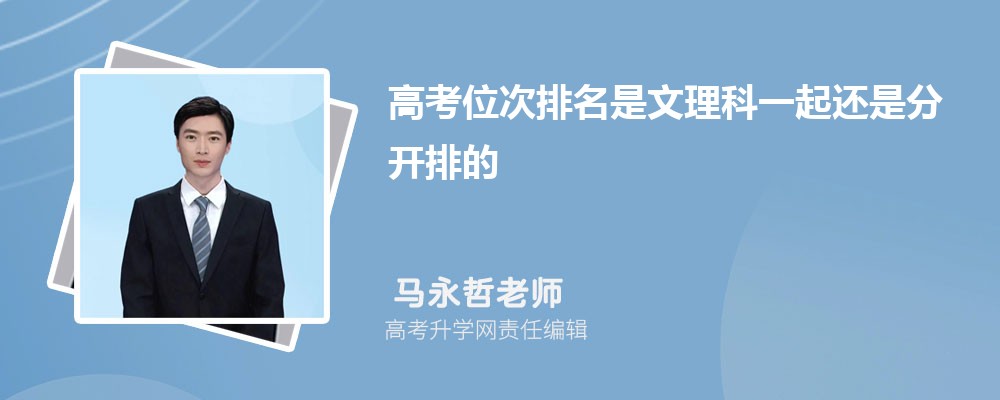十年再高考“所理解的教育”
更新:2023-09-19 13:34:52 高考升學網2018年安徽省高等職業院校分類考試在25日舉行,10年前的安徽“零分考生”徐孟南參加了人生第二次高考。
交白卷,是他當初刻意為之。2008年的高考,他在高考的每張試卷上違規寫下了個人信息和自創的“三人行教育”。他想獲得零分,以吸引公眾對其教育看法的關注。徐孟南所謂的“三人行教育”,大意是指從初中開始培養學生愛好,學習基礎知識,高中根據愛好分科,再通過選拔進入大學學習。
彼時的徐孟南更像是一個堂?吉訶德式人物,他以近乎偏執的倔強,成功引起了短暫的關注,但很快,他留下的只有“零分考生”的標簽。無論看來多么不可思議,我們仍需理解一個那時才十幾歲的少年,對龐大高考機器的抗爭。
十年時間,徐孟南用“打工、結婚、生娃、離婚、再高考”劃下并不出奇的人生軌跡。如今,當他再次走進高考大門時,無論他是否承認這是“浪子回頭”,著實是以一己之力,“詮釋”高考之于個人、之于社會的價值。
從教育價值來說,我們總是在問,高考對一個人到底意味著什么?徐孟南十年前經歷,很難可以用來說明什么。比如不能說不交白卷的徐孟南,就會劃下多么華麗的人生軌跡,但是,如果當初徐孟南收斂自己的偏執,努力備戰高考,并且得以進入大學,無疑是給人生更多的想象空間,最起碼,在大學之后,他可能會擁有更多的工作選擇。這就好比說,錢可能并不是什么好東西,但是,有錢確實能夠讓你多一些選擇。
從教育意義來說,我們也還在問,教育對社會的意義到底在哪里?尤其是還是一個仍存在積弊的教育體系。當年,徐孟南的厭學,厭惡高考,正是對高考制度本身存在不滿。對一個事物的不滿,它本身就是一個人的情緒,背后則是一個人的認知。你不能說他不對,但是,我們還是不得不說,他對高考意義的認知,顯然是片面的。
高考縱有各色各樣的缺陷,但是,它的存在本身,就意味著強大的正面意義。它作為公民知識修養的培養體系,它無疑是最有效率的機器;它作為國家人才選拔的選擇機制,它同樣無疑是最公平的。在沒有更好地體系和機制出來之前,它就是最合理的存在,何況,它一直在修繕它的缺陷,朝著更公平合理的方向趨近。
徐孟南說,他在十年后再次走進高考,“文憑對自己來說也不重要”,他只是希望有了更高的學歷,選擇工作的范圍可能更大。這句話其實是矛盾的,文憑本身就意味著學歷,他現在應該已經接受了文憑的價值。而“學歷意味著更多選擇”,這句話折射出他對高考的“新”理解。
頗有趣的是,徐孟南說他當初因為韓寒的一本書而厭學,而就在今年年初,韓寒寫了一篇題為“我所理解的教育”的文章。這個在少年時代也曾經討厭高考的男子,如今對高考有了更新的理解??學校和高考,是基本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;有文憑只是開始,但它是人生的標配。
十年再高考,本身就是對教育的再理解。理解萬歲,而彼此理解,可能更重要。
新高考走班制如何落地湖南校園? 高級研修班“指點迷津”2023-09-14 00:39:59
“0分考生”再高考:如果當時有人勸我 我一定不考0分2023-09-15 11:06:01
2019年高考報考:教育學專業與師范專業大不同2023-09-19 07:15:43
學生怎么減負?高考改革怎么推?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回應教育熱點問題2023-09-22 01:14:35
高考百科:什么是師范生免費教育(本專科生)2023-09-20 06:00:46
北大專家來渝交流新高考 近百名教育工作者參會2023-09-19 19:32:53
今秋入學高一新生將實行“新高考” 合肥多所高中開設“生涯規劃”教育2023-09-18 07:42:10
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中考高考教育熱點提案分析解讀2023-09-15 22:34:15
余黨緒:從40年高考命題的演進看思維教育的方向2023-09-18 13:58:57
千余人齊聚鄭州高新區 共話高考改革與教育2023-09-14 17:55:56
2019年浙江高考個人成績總排名查詢入口:愛揚教育2023-09-17 01:57:40
2019年甘肅高考排名查詢,甘肅高考成績排名查詢系統:愛揚教育2023-09-15 16:28:37
2019年河北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河北教育考試院】2023-09-19 12:21:02
2019年浙江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浙江省教育考試網】2023-09-21 04:03:48
高考志愿怎么填 教育專家支招解惑2023-09-21 11:57:39
2019年高考7日舉行 教育部門將嚴查違規作弊行為2023-09-20 03:40:01
高考園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2023-09-19 20:20:28
高考烹飪與營養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2023-09-16 00:14:35
高考食品營養與檢驗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2023-09-20 07:46:18
高考服裝設計與工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2023-09-19 06:23:12
2019年山東高考體育專業測試成績查詢:山東省教育招生考試院2023-09-17 14:03:22
高考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2023-09-18 17:13:35
廣西高考成績597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8:04:03
河北高考204分:河北高考204分能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8:02:35
河南高考522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2024-07-13 18:01:22
江蘇高考443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2024-07-13 18:00:06
福建高考成績45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9:03
河北高考成績57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7:40
云南高考成績32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6:12
浙江高考成績27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5:00
北京高考成績510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3:52
福建高考成績49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2:47
云南高考成績451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1:37
吉林高考成績285分可以上什么大學2024-07-13 17:50:10
新高考走班制如何落地湖南校園? 高級研修班“指點迷津”2023-09-14 00:39:59
“0分考生”再高考:如果當時有人勸我 我一定不考0分2023-09-15 11:06:01
 新高考走班制如何落地湖南校園? 高級研修班“指點迷津”
新高考走班制如何落地湖南校園? 高級研修班“指點迷津” “0分考生”再高考:如果當時有人勸我 我一定不考0分
“0分考生”再高考:如果當時有人勸我 我一定不考0分 2019年高考報考:教育學專業與師范專業大不同
2019年高考報考:教育學專業與師范專業大不同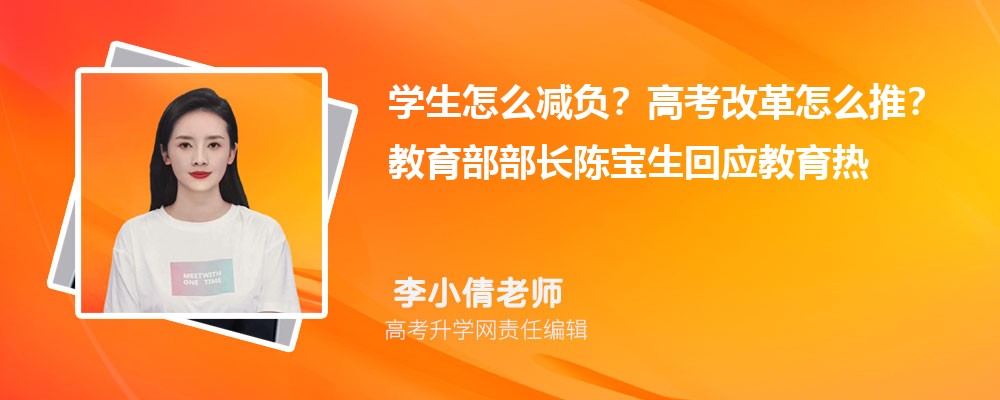 學生怎么減負?高考改革怎么推?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回應教育熱點問題
學生怎么減負?高考改革怎么推?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回應教育熱點問題 高考百科:什么是師范生免費教育(本專科生)
高考百科:什么是師范生免費教育(本專科生) 北大專家來渝交流新高考 近百名教育工作者參會
北大專家來渝交流新高考 近百名教育工作者參會 今秋入學高一新生將實行“新高考” 合肥多所高中開設“生涯規劃”教育
今秋入學高一新生將實行“新高考” 合肥多所高中開設“生涯規劃”教育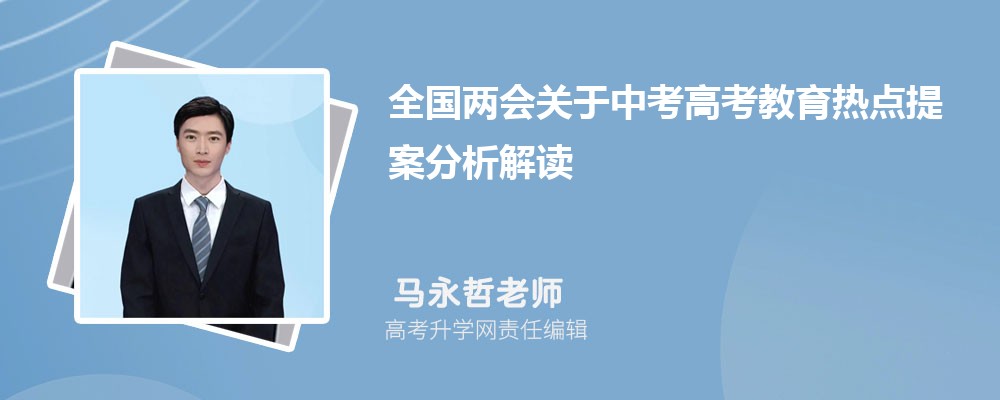 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中考高考教育熱點提案分析解讀
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中考高考教育熱點提案分析解讀 余黨緒:從40年高考命題的演進看思維教育的方向
余黨緒:從40年高考命題的演進看思維教育的方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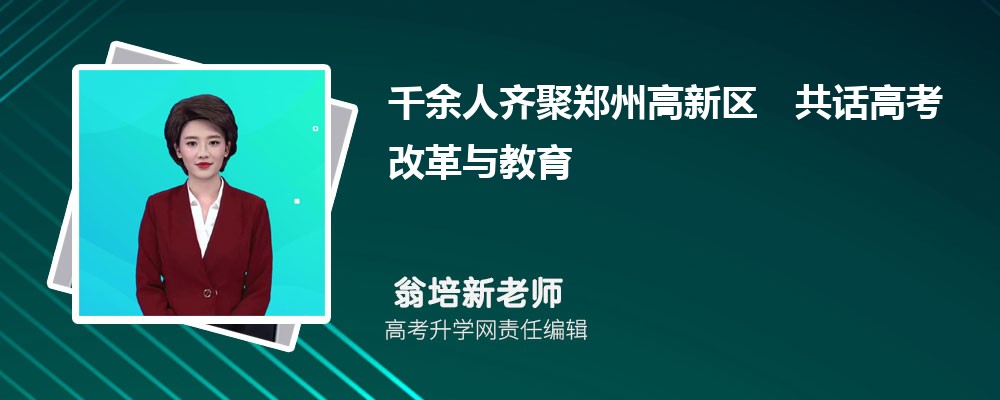 千余人齊聚鄭州高新區 共話高考改革與教育
千余人齊聚鄭州高新區 共話高考改革與教育 2019年浙江高考個人成績總排名查詢入口:愛揚教育
2019年浙江高考個人成績總排名查詢入口:愛揚教育 2019年甘肅高考排名查詢,甘肅高考成績排名查詢系統:愛揚教育
2019年甘肅高考排名查詢,甘肅高考成績排名查詢系統:愛揚教育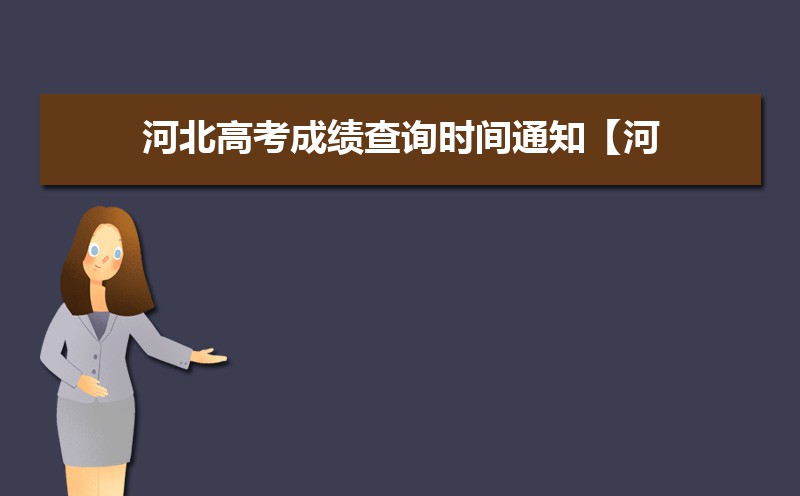 2019年河北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河北教育考試院】
2019年河北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河北教育考試院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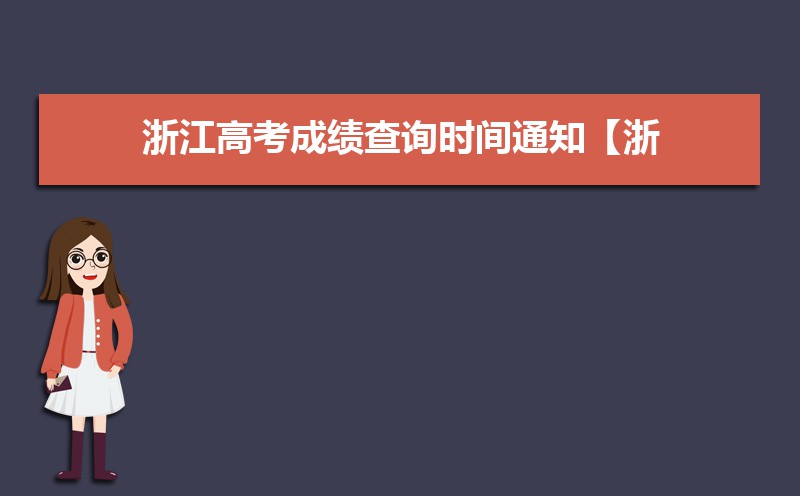 2019年浙江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浙江省教育考試網】
2019年浙江高考成績查詢時間通知【浙江省教育考試網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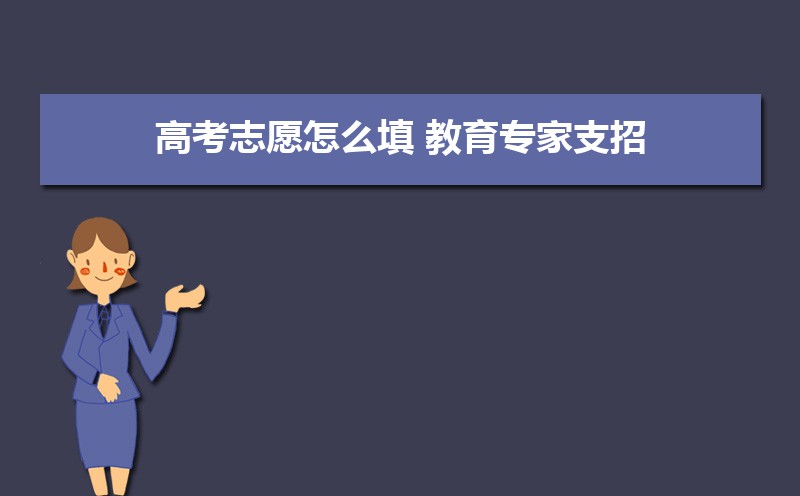 高考志愿怎么填 教育專家支招解惑
高考志愿怎么填 教育專家支招解惑 2019年高考7日舉行 教育部門將嚴查違規作弊行為
2019年高考7日舉行 教育部門將嚴查違規作弊行為 高考園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
高考園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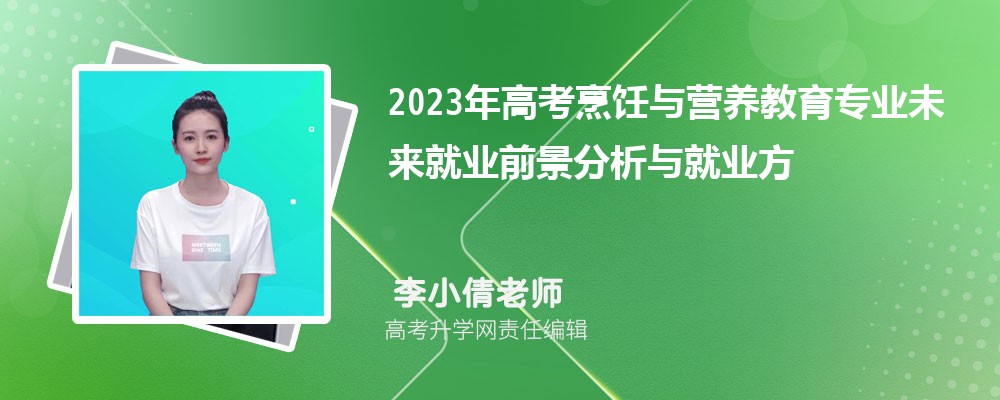 高考烹飪與營養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
高考烹飪與營養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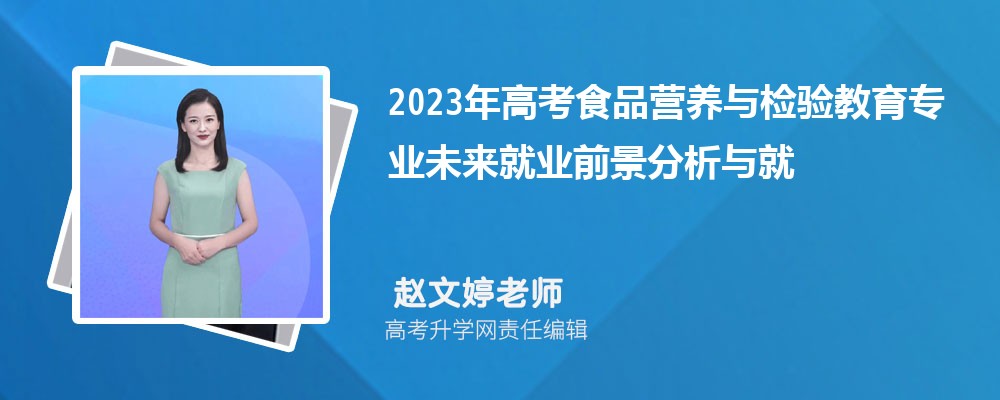 高考食品營養與檢驗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
高考食品營養與檢驗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 高考服裝設計與工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
高考服裝設計與工藝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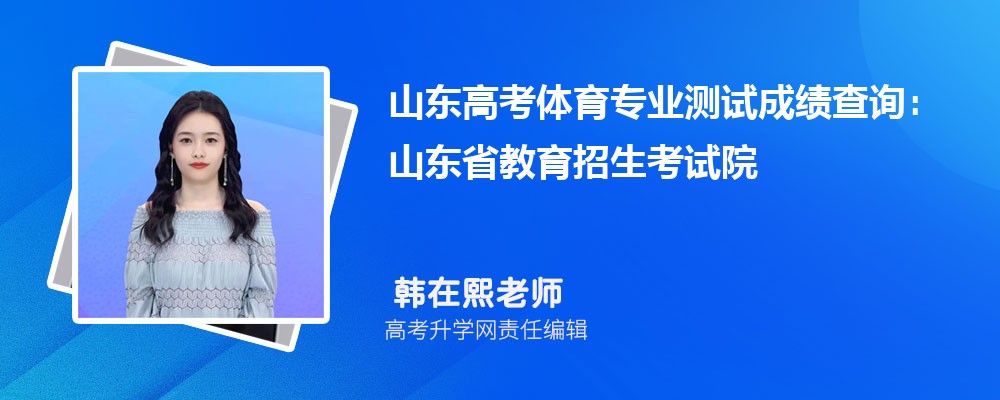 2019年山東高考體育專業測試成績查詢:山東省教育招生考試院
2019年山東高考體育專業測試成績查詢:山東省教育招生考試院 高考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
高考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未來就業前景分析與就業方向解讀 廣西高考成績597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廣西高考成績597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河北高考204分:河北高考204分能上什么大學
河北高考204分:河北高考204分能上什么大學 河南高考522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
河南高考522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 江蘇高考443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
江蘇高考443分左右的大學有哪些院校可以上 福建高考成績45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福建高考成績45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河北高考成績57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河北高考成績57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云南高考成績32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云南高考成績32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浙江高考成績27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浙江高考成績276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北京高考成績510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北京高考成績510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福建高考成績49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福建高考成績492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云南高考成績451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云南高考成績451分可以上什么大學 吉林高考成績285分可以上什么大學
吉林高考成績285分可以上什么大學